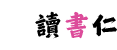离娄章句(上)41~50
41、孟子说的道 42、亲情孝道爱天下人 43、人与人相处之道 44、诚是基本 45、世事正须高着眼 46、什么是信 47、承欢膝下 48、谁明白善 49、天之道人之道 50、二老归服仁政
《孟子与离娄》孟子说的道
孟子曰:「道在尔,而求诸远;事在易,而求诸难。人人亲其亲,长其长,而天下平。」
他接着讨论下去。可惜文字都被后人圈断了。后世学者为了自己断章取义的方便,划分开变成了「章句之学」,实际上孟子的文字是连贯的,他的话还没有说完。
《离娄》这一篇首先提到尧舜,讲领导之学、帝王之道。现在这个问题连到真正的「道」,不是打坐修道的道,也不一定说治国平天下之道,这个「道」就是一个法则。政治有政治道德的法则,做人有做人道德的法则。总而言之,有个代名词叫做「道」,包括了我们现在大家要学佛修道的「道」也在内。孟子这句话到底是圣人之言,千古不易,没有办法撼动,没有办法修改。他说「道在尔」,就在这里,每一个人都有道,都在你自己那里,我们的心就是道,但是因为自己不知道「而求诸远」,拼命向外面去找,去求一个道,个个都是如此。
尤其是一般人,除了「自暴」与「自弃」以外,不大相信自己的价值,喜欢求些稀奇古怪。如果有人说要传你道,叫你先在门口磕三个头,然后搞些花样,越搞得神秘,你越觉得有道。这就是因为人心里有一种空虚,所以社会上才出来这许多的花样。实际上真正的「道」并没有这些外形,「道」就在「尔」,很近;「尔」就是你,就在你那里。
这个地方我们引用禅宗六祖一句话,六祖给一个人传道以后,这个人就问,除了这个以外还有秘密没有?六祖说,秘密有啊!他问秘密是什么?六祖说在你那里,不在我这里。一般人自己都找不到,看不清自己,这就是最大的秘密。所以孟子说「道在尔」,也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可以有趣地说孟子这一下也是在传密宗,这个秘密在你自己身上。
「事在易,而求诸难」,这第二句话更重要,天下没有什么难事,每件事情都很简单、很容易,都是人自己玩弄聪明把它玩成复杂困难了。但是你告诉他容易也不行,所以人的一般心理,古书上叫做人情,就是人的心理都是「重难而轻易」。越困难,他越看得贵重;越容易,他越看得没有用。我常跟年轻同学讲,我都告诉你了,你不相信;一定要等到我死后有人叫好,你才觉得我说得对、说得好吗?因为人情也「重死而轻生」,死去的都是好的,活着的并不好;人情也「重远而轻近」,远来的和尚会念经,本地的和尚不一定行;人情也「重古而轻今」,古代的就是好的,现代人都不行。现在的人是「重外而轻本」,外国来的学问都是好的,自己国家的都是狗屁,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自己本土的大又圆。
这真是一个笑话,如果我们这一堂研究《孟子》的人,照个像留下去,后世的人会说:哎哟,他们这一代人好了不起喔!算不定大家还跪在前面,向我们磕三个头呢!可是我们都看不见了,对不对?这是人情。
同样道理,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处世做人的原则。现在研究心理学、懂了心理学的人,就应用这种心理,故意弄得错综复杂一点,人们就信,成为领导群众的法门了。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叫人来参观,电梯一上来就到了,是没得价值的;最好电梯不开,十楼要慢慢走上去,然后这里弄个栏杆,那里给他一个弯曲,就有味道了,人的心理就是那么一件事情。
所以啊,天下的道理,不管做人做事,或政治、社会问题,都是同样的。你把这个书读懂了,原则也就都懂了。
《孟子与离娄》亲情孝道爱天下人
《孟子》这一段,是关于领导学的结论,他说「人人亲其亲,长其长,而天下平」。换句话说,还是人的问题。他说社会上每一个人若能做到「亲其亲」,爱自己的父母子女,也爱天下人的父母子女;爱自己的兄弟,也爱天下人的兄弟。对天下任何人都像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样好,才是仁道。
不过这个仁道是有其逻辑性的,是由己而推及于人的。「亲亲之仁」是儒家道理,对自己的父母好,推而广之,对他人的父母也好;再行有余力,对更多人的父母好,一层一层推广开来。后世儒家和佛家各执己见的论议,也在这个地方。
宋代有人对此有争论,由于佛家说你们儒家这个「仁」啊,固然是好,但不及我们佛家的慈悲伟大。儒家则说,对啊,你们的慈悲是真好,但不及我们的仁义实际,两个观点不同而起争论。这个儒家的人说:我问你,释迦牟尼和孔子两人的妈妈都掉到河里去了,你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跳下河去先救谁的妈妈?如果先救孔子的妈妈,那是不孝,还能够当佛吗?如果先救自己的妈妈,后救孔子的妈妈,你那个慈悲就有亲疏先后了。而我们儒家,孔子「噗通」跳下水,一定先救自己的妈妈,自己妈妈救起来以后,看到你的妈妈还没有救起来,再下去将你妈妈背上来,这是我们儒家。
其实宋儒这个争吵,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懂佛经,佛学的所谓大乘菩萨道,也是这个亲亲仁民之义,也是一步一步的。后世学佛的人解释大慈大悲,是笼统的说法,不是这个道理。如果说我对在座诸位一切慈悲,我没有这个力量,做不到,不可能的。虽有这样一个心,就是孟子讲的,「仁」是像精神的房子一样,心要时时住在这个「仁」的房子中。「义,人之正路也」,要照程序来,不是笼统。
孟子为什么在这篇里谈到「事在易,而求诸难」?所以用四个字告诉青年同学们,中国人读书研究学问,很简单,需要「好学深思」,深深去想,去思考其中的道理。他为什么这样讲?「道在尔,而求诸远;事在易,而求诸难」,你不要断章取义喔!从《离娄》第一句话开始到现在,他是对那些当领导的帝王们感叹,真的没得办法了,因此说「人人亲其亲,长其长,而天下平」。可见那些上层阶级的领导人都做不到「亲其亲」,都做不到「长其长」,他们连自己家庭都做不到亲爱仁慈,如何能够要求社会?!所以那个时代的乱,每个时代的乱,并不能够责怪一个领导或一个团队,因为整个的社会都发生了问题。
所以我最近常常告诉大家,为什么孔子孟子提倡孝道,提倡仁义?可见人类对于孝道是知易行难,知行难以合一的,在仁义之道上也是一样。对不对?是不是?所以孟子极力提倡,要人人能够「亲其亲,长其长」,这样天下才能平。可是啊,人不能做到,所以天下乱了。社会之乱、世界之乱,是基于人心而来的。这是这一段第三个道理。
第四个道理呢?就是我们个人基本的修养是不是真能做到「亲其亲,长其长」?很成问题。譬如讲孝道,有时候情感来了,孝很容易,也做得到;长久就难了,恒久性更难。关于这其中的道理,孟子在下面就提出来了。
《孟子与离娄》人与人相处之道
孟子曰:「居下位而不获于上,民不可得而治也。获于上有道,不信于友,弗获于上矣。信于友有道,事亲弗悦,弗信于友矣。悦亲有道,反身不诚,不悦于亲矣。诚身有道,不明乎善,不诚其身矣。」
这一节不是孟子的话,是子思在《中庸》里的话。子思是孔子的孙子,他不是孟子的老师,子思的儿子叫子上,孟子是跟子上学的。另又一说,很难考据,说孟子十岁的时候去见过子思。子思跟这个童子谈了几句话,就对他非常客气非常有礼貌。有些学生的家人很不高兴,子思说:你们不要轻视他,那是将来的圣人。古书上有此一说,究竟靠不靠得住都不知道。不过,孟子的确是私淑于子思,私淑于孔子这个系统。
这一段《中庸》上的话,是孟子引用来的,不过少了引用两个字。如果现在,一定会去打官司,认为孟子侵害子思的著作权,没有加上一个「子思曰」。
说到「居下位而不获于上,民不可得而治也」这两句话,不免想到古代读书人的艰难,因为要想考功名啊!可是有些考试官是刁钻古怪的,算不定就拿这两句话当题目。突然一个题目发下来,出在哪一段有时候就想不起来,所以以前的人读书也真可怜。这个中国帝王用考试取士的方法,害了中国一千年,不但科学受害,一切思想与文化也都受害。是谁发明这个专利啊?不是唐太宗,而是隋炀帝的祖宗,发明以考试取士的方法。不过用这个方法最成功的是唐太宗,在第一期的学生考取后,唐太宗站在高台上召见,考生磕了头,再请他们吃饭。这时候,唐太宗把胡子一抹说「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」,第一流的头脑都被我收进来了。读书人一个字一个字,磨炼了几十年在书本上,你说难不难?一点背不熟,题目一出来不晓得出在哪一句,就完了。
现在我们回过来看本文。「居下位而不获于上」,问题在这个「获」字。什么叫下位呢?譬如我们当一个里干事,行政的公务员或者一个管区的警员,这是行政上最基层的,也就是下位之下位,基层的下位。下位并不是难听的话,而是最基本的那一阶层,或者是我们当一个幼儿园的老师,也是教育的基层。
讲到这里我倒也有点感慨,像幼儿园老师,我经常想去当,人家都说我没有资格,不合规定,所以我没有办法。我也很想到阿里山去弄个小学教师当当,万万想不到也不合规定,所以上位也不能居,下位也不能占,那只好变成个「无位真人」。
现在是「居下位而不获于上」,古人的解释说在下位的人没有被上面长官欣赏,不知道你这个人;或者是因为官做得小,皇帝当然不知道你。「民不可得而治也」,老百姓不可以得到治理,换句话说,老百姓治不好,政治就做不好。照文字解释是这样。两句连起来,就是因为在下位位子太小了,上面并不信任我,因此,虽有政治的天才,可以把国家天下治好,却没有机会施展我的抱负。这种解释比较合理吧!
那么怎么能「获于上」呢?我们现在先讲文字。我是个在下位的人,想使上面人知道我,除非我长高一点,排到头排,上面人过来点名就先看到我了;假使我长得矮,他点名到后面都疲倦了,我举个手他也看不见了。所以啊,想要获于上有道,把鞋跟垫高而已矣!当然这是说笑话,要想上面人知道你,是有方法的。
孟子不是那么说的,他说「获于上有道,不信于友,弗获于上矣」,如果朋友都不相信你,上面就不会知道你。换句话说,照文字上解释,原来要拉关系就要交一个有背景的好朋友,地位高一点,反正替我吹一吹嘛,就可以得到上面的赏识了。
再看下去,拉关系也是有方法的,「信于友有道,事亲弗悦,弗信于友矣」,要想向朋友拉关系,先要把父母兄弟姊妹关系处好,如果家里都不和睦的话,朋友也不会相信你。这又要从道德上来讲了,对不对?那么,「悦亲有道」,在家里对父母兄弟姊妹也有办法,什么办法?「反身不诚」,就是回转来看自己对人是不是诚恳。
假设自己对父母孝顺、对兄弟姊妹友爱是手段,不是真诚,而是为了明天向爸爸要钱用,这就不是诚恳啰,「不悦于亲矣」,父母心里当然不高兴。
那么怎么做到「诚身」呢?要注意喔,不是「诚心」而是「诚身」,身体这个「身」。「不明乎善,不诚其身矣」,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,自己本身就做不到真诚。这个说得就很严重了。
我们小时候读书读到这里,就问老师:先生啊,这一段怎么讲呢?老师大概把文字告诉你一下;然后你再问,老师就说:背来!现在你不会懂的,以后长大了会知道。当然,老师那么讲,我现在很恭敬他,果然我年纪大了是知道了;不过我知道的不是他知道的,不是他那一套了。所以你们要注意,看几十年前那些反对旧文化的文章,反对的是哪一种形态的?现在已经把文化与文字的根都拔掉了,还有什么可反对的啊?连反对的对象都没有了。
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段,牵涉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,就是一个「诚」的问题。
《孟子与离娄》诚是基本
「是故,诚者,天之道也。思诚者,人之道也。至诚而不动者,未之有也。不诚,未有能动者也。」
孟子引用了子思这一段以后,下面说「是故,诚者,天之道」,所以说,「诚」这个东西是天道,这是孟子下的结论,不过到我们手里又要另下结论了。什么叫做天道?是天主教那个道吗?还是回教清真寺那个道?还是大乘学舍这一道呢?都是天道啊!所以这个道也是问题,天道是什么?拿禅宗讲,这是个话头。
孟子接着又提了一个话头给我们,「思诚者,人之道也」,「诚」是天道,「思」是思想,思想达到那个至诚的境界就是人道。对不对?这个文字,假使我不提出来,青年同学们也会忽略。
什么叫「思诚」?我们研究分析这个字眼,大概就是思想的诚恳了。谁的思想不诚恳啊?譬如说我们隔壁是小美冰淇淋店,心想大概还有十分钟下课,下课以后我们去吃冰淇淋。这个时候啊,是三分心意在听《孟子》,七分心意是吃冰淇淋,当然是最诚恳的时候了。照这样说来,吃冰淇淋是人道啰!听《孟子》难道不是人道吗?这都是问题啊!这问题要做科学的分析思考,所以又是个话头了。
「至诚而不动者,未之有也。不诚,未有能动者也。」他说心念到达了「至诚」,一定有「动」,不动是不可能到至诚的。「动」什么啊?如果「至诚」都动的话,只要我们「至诚」一下,汽车就可以开动了,做得到吗?
他是强调这个「诚」,「诚」就是动能,真要动起来必须要「至诚」,「不诚」的话不可能「动」。那一「动」,在古人讲是「动情」,「至诚」就「动」。譬如我们这个菩萨摆在后面,我也很「至诚」,天天跪在那里,请他动一下,他绝不动,除非地震的时候,那不是我的「至诚」。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大,这节书的内容问题就大得很,是孟子讲的真工夫、真学问,可以说是孔孟之道的密宗。
《孟子》这一段引用了子思的话,我们做学问怎么办呢?青年同学回家去翻《中庸》,先看子思这一段。《中庸》很简单嘛,不过你们读得慢一点。子思在《中庸》里最强调的是这个「诚」,以及「诚」的境界。诸位学佛学道的朋友,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是必读之书。《中庸》里说「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」,这就是顿悟之路,类似禅宗的顿悟;后面讲修养,就是渐修做工夫之路。他一步有一步的工夫,一步有一步的境界,都是属于心行的修养。所以孟子在这里提出「动」来,属于动心忍性的修养。这是工夫啊,他特别引用子思《中庸》中的那一段,因为与他说的「动」有密切的关系。
我想这个问题啊,诸位尽可能下一次来上课以前,把《中庸》里关于「诚」字的精义先行研究一下,我们讨论起来就方便了。当然最好来上课以前看,因为如果你今天回去看了,再过一个礼拜来上课,你那个「诚」恐怕就忘记了,变成「不诚」了。
这一段与前面孟子讲的「为政不得罪于巨室」有关系。前面讲到「居下位而不获于上」,大家要注意,在这两点上面不要有这么大的误解。照文字的解释,他说我们没有出头,或者是官做得很小,居下位,而不能得到上面的信任,上面当然指各国诸侯的君王了。「民不可得而治也」,如果上面不信任,政治的推行就很难了。换句话说,我们讲土一点,一个人要想做一番大事业先要找个靠山。
就像昨天有个朋友,山上有很多地,要捐给我们,我说不要;他一定拖去看,说怎么好怎么好。结果爬山爬到上头一看,我说这个地方没得风水,不要。为什么?没得靠山,然后就在那个山头上乱谈了一番风水的道理。我说靠山很重要,做人也一样,坐椅子要找个靠背椅。这个孤伶伶的山顶,没有靠山。万一台风来的时候,八面受风,房子怎么盖啊?同样的道理,这也是「不获于上」啊,上面没有靠山,要想做事也不好做。
前几年我在警务处演讲的时候,华视正在上演包公,因为我们的朋友萧先生在华视当总经理,他就请我去讲包公。包公很好讲,但是我说包公之所以是清官,后面有个靠山支持啊,就是宋仁宗支持他嘛。如果上面不信任他的话,这个清官怎么做啊?所以包公固然是清官,但大家忘记了有了清明的皇帝宋仁宗支持,他才能做清官。
这个道理我们简单地说,不要扯远了。圣人不是叫人拍马屁以得到上面的信任。什么叫「居下位而不获于上」呢?一个人要有高见,这个上并不是讲皇帝的上位,而是讲远见。
中国古人的话,「取法乎上,仅得乎中」,一个人如果立志效法要做圣人,圣人做不到,至少会成一个有干才的贤人。如果一个人立志只要做一个有干才的贤人,万一达不到目的就等而下之什么也没有了。换句话说,你想做生意发财,发个一千万美金,弄不到的话,也可以弄到几百块钱嘛!如果说你一辈子只想三千块钱一个月,算不定一个月五百块钱都赚不到。「取法乎上,仅得乎中,取法乎中,仅得乎下」,所以我们读孔孟之书想做圣人,做不到的话,至少还有一个人的样子。
昨天我跟一个同学讲到发财的问题,我说前天看了一本书,明朝人作的,说有一个人读了一辈子书很穷,隔壁这一家人也不读书但有钱,实在奇怪。有一天他忍不住就问这个有钱人,你那么有钱,有秘诀没有?他说当然有啊,你回去先斋戒沐浴三天,我也一样,然后我传给你。三天后他去了,那个大富翁坐在大堂上,他说人为什么不能发财,你知不知道?因为人心中有五贼,这五个贼把你偷光了,要把这五贼赶出去,你就会发财了。哪五贼啊?仁义礼智信,你把这五贼全赶光了,我包你发财。这个读书人一听啊,算了,我读一辈子的书就想要仁义礼智信,这些赶光了我还做什么人啊?因此就回家了。
这一本书写到这里为止,下面有批,说仁义礼智信都赶出去了就会发财,那我还叫什么人啊?我也在下面批,我批的是「这样就叫做富人,有钱人」。所以「不获于上」,同样是这个意思,禅宗的话就叫见地,一个人要有高度的智慧,有远见,做人也好,做事也好,人没有远见人生已经差了一截了。
《孟子与离娄》世事正须高着眼
记得很多年前有个朋友当外交官,要出国去,一定要我写一张字给他。我说几十年没有拿笔,我那两个字难看到极点,他说反正非写一张不可,结果我就写了两句元代人的诗:「世事正须高着眼,宦情不厌少低头」,世间上的事情靠你有远见,就是「高着眼」。
有一天这位外交官请客,有二十多个人,就研究我写给他的这第二句话,「宦情不厌少低头」。做官的人究竟应该多向人家低头拍马屁呢,还是说不必要太拍马屁你?这个「少」字原意究竟是哪个意思?我说我只晓得照抄,至于原意,你问那个元朝作诗的人吧。不过我也认为这个「少」字太妙了,是双关语,必要的时候你多低一点头也可以,要做文天祥就不必低头了。其实岂止宦情做官呢,你们大家在做生意也可以换一个字,「商情不厌少低头」,该赚的钱就赚,狠起心来你也赚,不该赚的钱就不要,就不低头了嘛!教书的人,教情嘛,也不厌少低头,是一样的。
「世事正须高着眼,宦情不厌少低头」,这就是说,世界上的事情,在任何一个时代,任何一种环境,有头脑、有智慧的人都不会被现实所困。因为透过现实看到未来,透过一点而看到整体。这就是人世间应有的「见地」--「世事正须高着眼」。
《孟子与离娄》什么是信
其实这里每一节都很有深义的。「获于上有道,不信于友,弗获于上矣」,这很严重了,他说你获得上面的信任「有道」,是有个办法的,什么办法?要「信于友」,如果不「信于友」,你就不能「获于上」了。照这个文字解释也对啊,但是不是这样呢?这是孟子玩文字,很多古人的好文章因为玩文字玩得使后人看不懂,走错了路;不过有个好处,后人从这里去研究就可以写论文拿学位。尤其是《老子》,只写了五千言,三千年下来不晓得多少人写有关《老子》的文章,各有各的老子。如果老子看到一定笑死了,心想我不过才写了五千个字,你们写了几千万字还没有写完。《孟子》这本书也是这样,后人写得太多了。
那么我们就要研究了,如何「信于友」呢?第一我们先了解儒家的思想。孔孟的思想讲信,普通我们解释这个信字很容易,读古书都晓得,信者信用也,就是有信用,讲话说了算数,这叫「言而有信」。如果这样解释的话,你把《孟子》全书读完了,会感觉孟子自打耳光,因为孔子说过「言必信,行必果,硁硁然小人哉」。孟子自己也讲过的,「言不必信」,对不对?讲话不守信用是可以的;「行不必果」,做事情也不一定要有交代,如果一定交代、一定守信用,就是小人。所以读古书很难,上下文要连起来才会明白。
「言必信,行必果,硁硁然小人哉」,孔子这句话是讲某一类的事。譬如古代有个人最守信用,名叫尾生,他跟女友约在桥下相见,等的人没有来,山洪爆发,他为守信用最后抱着桥柱子被水淹死了。他守的什么信用呢?爱情的信用,不是别的大事,这一种人就是所谓「言必信,行必果,硁硁然小人哉」。又譬如假设我们碰到一个坏人,因大意而答应了他,后来发现他是坏人,你为了守信用也去当坏人吗?那就是「硁硁然小人哉」,孔子讲的就是信字的第一个道理。
第二个道理,什么是信呢?如果只照字面解释孔孟之学,就难怪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了,这是几千年来照字面错解而造成的。什么叫信啊?信自己,也信任人家。所以朋友之间要有信,信任自己,能够有自信,也信任别人。「信于友」这个友,并不一定是讲一两个朋友哦,儒家所讲的友与弟就是社会的关系。友弟就代表社会,如果自己的兄弟姊妹都相处不好,是不可能对社会对朋友好的。所以「信于友」是这么一个道理。「不信于友,不获于上矣」,一个人如果不信于友,他的人品格调已经不高了,器量也不宽厚了;就像下棋、柔道一样,段数已经不高了。
「信于友有道,事亲弗悦,弗信于友矣。」他说人要做到兄弟之间信于友,也是有方法的,第一是事亲,就是孝顺父母。这里为什么不讲孝而讲事亲呢?事就包括侍奉,侍候奉养。侍候跟奉养是两个观念哦,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讲养亲,说孝养有个道理的,孔子讲:「色难」。什么叫色难?色是指态度,如果你给爸爸几千块钱,说拿去!这个态度我做爸爸就不接受,我就会说***,拿回去。所以我说小儿女向父母要钱用啊,是躺着来要;太太向丈夫要钱,是站着来要;如果父母向儿女要钱,是跪下来要。这个话看起来很伤心,不过,古今中外社会的演变就是这样。
说到色难两个字还有典故。明朝永乐时代有一个有名的才子叫解缙,是个神童,七岁就能够写文章,诗也作得很好。有一天永乐皇帝跟他一起走路,古人读书讲究作对子,永乐皇帝讲:《论语》上这个「色难」啊,很不好对。解缙说容易啊,永乐皇帝等了半天又问,你讲容易你怎么不对?解缙说我对了啊,「色难」对「容易」嘛!那对得非常工整,这就是才子之所以为才子也。
讲到色难,「事亲弗悦」就是色难。现在对父母的孝道问题更多,我有好几个学生都在外国,二老仍在台湾。有一个学生,媳妇也非常孝顺,要接二老去美国奉养,可是二老考虑了半天还是不去。我这个学生就把儿子抱回来,他说那二老真高兴啊,可是临走到飞机场时媳妇把孩子从婆婆手里接过来,二老眼泪掉下来了,看了很难过。所以「事亲弗悦」,太难了,孝养不是那么容易。时代到了今天,我自己早就准备好了,公公也不做,外公也不做,因为我是半个出家人,这些同我都不相干。如果当个在家人碰到这个情境,五味俱陈,事亲要悦,真讲孝道真是太困难了。
如果「事亲弗悦」的话,那就「弗信于友矣」,对于其他人就谈不到可信了。扩充些去讲,这个就是教育问题。讲到一个人的修养,都属于教育问题。所以我经常说,中国文化的教育目的,是教育一个人完成完整的人格。所以大学之道是完成为一个大人,做一个真正的人,这是教育的目的。《孟子》这一段也是说教育目的,一个人要完成真正的修养,就是刚才解释过的,要事亲有道才能信于友。
《孟子与离娄》承欢膝下
第四段来了,他是一段一段地讲,「悦亲有道,反身不诚,不悦于亲矣」,他说想要孝养父母有道,先要回过来问自己。我们读古书出身的,对父母都很孝顺哦。说老实话,我一回家看到父亲还会发抖的哦;我父亲已经对我很客气了,可是父亲始终是有威严的。我从小养成的规矩,父亲一到前面,我赶快站起来。只有父亲躺在床上高兴的时候,问我十多年在外面都搞些什么,只有那时心情才放松一点,平常总是很严肃的。这是老的教育,你们没有看过,我生在这个时代的夹缝,受的是新旧教育,古今中外味道都尝过了。所以你要真讲孝顺,是「反身不诚」,问自己内心。
我现在回想,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家里住了一年,我觉得这一年当中至少做到了使父母悦,是真的高兴。不过时间太短了,现在想起来都很难受,所以我经常说到黄仲则的诗,感人肺腑。开始讲《孟子》的时候我曾讲过这首诗,「惨惨柴门风雪夜,此时有子不如无」。对于我自己的母亲,我经常有这个感叹,现在已九十多岁了,虽然她晓得我还活着,但是想到「此时有子不如无」,就觉得自己是个不孝的儿子,这是遭遇时代的影响,有这个儿子等于没有(编按:怀师的太夫人一九九〇年百岁仙逝)。
可是在家里的时候啊,我曾经反省过自己,我十几岁就离家,十年后回去不过相处一年,所以我再出门的时候,父亲就拍拍我的背,他说你要走了,不过我很高兴,我有个好儿子。他虽然很痛快地讲,但是我晓得此次一别就不知何年何月再见了。
再回来讲《孟子》吧!这一节中每一段、每一节都有方法的哦,不是呆板的信条,如果大家把孔孟学说当成信条那么信,你们就读错了,叫做不学无术;既然读了书,就要学而有术,术是方法,不是手段。孝顺父母,友爱之道,获于上之道都有方法的,这就要博学慎思了。学而有术不是用手段,你把术完全解释成手段就错了,所以说「反身不诚,不悦于亲矣」,就是这个道理。
一节一节下来,这个孟子像在打鱼一样的撒网,就是现在青年同学们讲的在盖,盖得很大,从「不获于上」,一路盖下来。像我们撑的雨伞一样,撑开来很大,手抓的伞柄只有一点,那就是中心点,要到最后才会告诉你。
再说到诚,「诚身有道,不明乎善,不诚其身矣」,更严重的问题来了,诚也是有方法的,我们解释诚很简单,就是诚恳。譬如说你碰我一下,我说讨厌,你不能说我这句话不诚恳啊,不是假话,对不对?有人要借用我的东西,如果我不想借给他,但又说拿去吧,这就是不诚恳了,对不对?所以什么叫诚恳,我们研究看看,如果说对人态度好就是诚,但明明看到这个人很讨厌却说他好,这也是不诚恳。所以诚恳是很难研究的。孟子在这里下一个定义,我这一句话要注意啊,孟子在别的地方不一定是这样讲。同时还要注意《中庸》,《中庸》专讲诚,对诚字的解释又有不同,方向不同,原则一样。
《孟子》这里怎么解释呢?「不明乎善,不诚其身矣」,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会诚。先不讲什么是诚,现在为了了解这个诚字,先了解《孟子》所讲什么叫善,其次要知道什么叫明。要找出《孟子》的善在哪里,先要找《尽心篇》,孟子在这一篇中所说的善与学佛打坐一样,有工夫的,不是偶然的。《孟子·尽心篇》里说「可欲之谓善」,这是孟子学问修养的真正工夫。
《孟子与离娄》谁明白善
前面在《公孙丑篇》中提到过养气,养我浩然之气,这也是真工夫,孟子有实际的经验。《尽心篇》也提到养心,不过养气与养心不同,养心是心理的修养,养气是对于身体的修练,两个则有相连的关系,所以孟子是有真实修养工夫的。
在《尽心篇》里,孟子提出来的「可欲之谓善,有诸己之谓信,充实之谓美,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。大而化之之谓圣,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」,这是一段一段的工夫修养,最后到成仁的境界。我们大家做工夫也是一样,乃至学佛、修道、打坐,或者练气功、练拳术。当一件事做到了可欲,舍不得离开,一天不做就不过瘾时,这样的可欲才叫做善。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那你根本连起步的境界都谈不上,善性当然没有,还谈什么修道,谈什么做学问啊!因为你没有做到可欲的境界。
可欲,不管你学佛也好,修道也好,做人也好,修养没有达到可欲的境界,没有达到废寝忘食的境界是不会成功的。也就是说,整个的身心都投进去,才是可欲的道理,可欲才叫做善。假使学问修养没有达到可欲的境界,没有变成欲望,变成习惯,永远在那里浮沈,就没有达到善。
现在再解释什么叫做诚。「诚其身」,这个里头问题还很大,第一步达到「可欲之谓善」,第二步做到「有诸己之谓信」,学打坐修道的人,工夫到身上来了,有效果来了,自己知道,叫做「有诸己」。譬如我们写毛笔字的人,我过去也练过字,练到什么程度?坐在那里跟人谈话,这个指头在写,想那个字的味道;味道够了,赶快拿笔一写,又悟到一个道理,原来这样一钩才有功力,才合于书法,这就是「有诸己」。
「有诸己」就是要上身,孟子也讲「不诚其身矣」,没有做到功夫上身,就是「不诚其身」。你是身体打坐呀,盘起腿来叫做修道啊?当工夫到你身上的时候,你找到自己了,有诸己则为信,有消息了。
由这一步到「充实之谓美」,慢慢就充实起来。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」,发光了,但是这个光不是有相的光明,不是物质、物理世界的光,而是智慧之光。「大而化之之谓圣,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」
你看孟子的工夫一步一步的,是孟子的密宗。孔孟都有他的密宗,他这个密宗方法传给你了,你把浩然之气那一段配合起来就会知道,孟子的确把工夫、学问、修养的心得都告诉你了。
现在还没有讲到《尽心篇》,将来讲到这一篇的时候,恐怕要讲得很慢了,因为内容很多,问题也很多。
现在回转过来,看孟子所引用《中庸》的话,「不明乎善」,善要明,乱做善人是不明。我经常告诉一般同学,做好事那么容易吗?我们有时候要做好事、种善因,但是反而得恶果。昨天正讲一个同学,别人有病,他把这个人当成他自己一样,热心的不得了。我说你真是莫名其妙,这个病人还有家里的人啊,会有意见的。你要晓得古人说「贤不荐医」,聪明人不推荐医生,更不推荐药给人家吃,因为吃好了应该,吃不好你怎么办?别人家属会一辈子骂你,恨死你。我说你以为是做好事,而且你又是那么主观,认为非这样医不可,你凭什么?你有把握一定会医好吗?万一这样死掉呢?怎么办啊?你心是好啊,方法不是那样的,不是你一个主观可以处理的。
所以,光是一味晓得这样是善事,你也是主观,并没有明乎善,要明才对。所以《老子》所谓「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」,能够了解一切人,这是有智慧的人;自知者明,能够自知才叫明白人。智慧人还容易找啊,明白人找不到,因为人都不大容易自知。
所以「不明乎善」这四个字非常简单,但是明善的确很难。再说如何是一个明白的人,我们引用禅宗的话做批注,真正明白自己、明心见性的人才够得上说一个善,不明白的不算善。那么这个明白也有它的层次,什么叫做明白?这是一个问题,所以《孟子》这个书看文字都好懂,非常好懂,但是你看,刚才我们随便一抓问题,已经讲了两次课、四个钟头了,还没有把它弄清楚,小的问题都已经那么多了。
他说「不明乎善」,此身不会诚。这里要注意哦,他是说此身不会诚,没有讲此心不会诚哦,问题是身要诚。这里要特别注意,不要马虎读过去,任何一个字都不能马虎。至于讲心诚,上庙子去拜拜或者上礼拜堂去忏悔,你说那个心诚不诚?绝对不诚。哪个人心诚啊?只有快死的时候,或者危险要命的时候,那个时候的祈祷跪拜绝对心诚。所以心诚已经很难,更何况《孟子》讲身诚,更难了。你如果要真做到善与诚的境界,照儒家的道理,所谓变化气质是由明乎善而影响到心理的转变,再由心理而转变心力,把整个生理都转变了,才能达到身诚。
在座许多学佛的打坐的人,搞得身体可怜兮兮的,因为你的心还不够诚,真诚的话生理为什么不能转变呢?佛学讲一切唯心,心能转物嘛,不能转就是你的心不诚,理也没有明,据我所知道的是这样。所以由心理影响到生理转变,由头发到脚趾尖,每一个细胞都是至诚的,至诚也就是学佛的修定工夫,至诚是必定的,那自然就定了。你不能定,因为你的心散乱,虽然道理说得很高,叫你心能够定,打死都做不到,那怎么叫诚呢?
《孟子》这里讲「不明乎善,不诚其身矣」,其中的内在意义包括了那么多,所以叫大家读书不要马虎。「不诚其身矣」,不是不诚其「心」。因为我们平常读《孟子》「不明乎善,不诚其身矣」,观念里头就变成诚其「心」了。更何况诚心都做不到,进一步诚身更做不到了。这一句话只能简单讲到这里,详细讨论起来就太多了。
《孟子与离娄》天之道 人之道
这一段是孟子引用《中庸》的话,那么孟子自己的意见是「是故诚者,天之道也;思诚者,人之道也」。孟子点题了,作文章一样,题目中心他给我们点出来了。孟子说所以诚这个境界、这个修养,是「天之道也」,合于天道,这个天是理念的天,与精神世界形而上那个功能、那个法则是相合的。
诚的本身是天道,这个天地是至诚的,有一句话「至诚不息」,所以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很大,真到了至诚,不息就是不休息。怎么不休息呢?就是《易经》上「天行健」,这个宇宙永远在转动,地球没有一分一秒不在动、不在转,如果这个地球一秒钟不转,乾坤息矣,我们就完了。
好几年前有个大学者,当代的思想家,他说中国文化讲天地是静态的。我不好意思批评,因为我批评起来就不好听了。我说中国文化谁跟你讲天地是静态的?中国文化讲天地是动态的,「天行健」,永远都在动,所以「君子以自强不息」,叫人要效法天地,永远不断地前进。我说哪里有讲静态的文化?出在哪一部书?真是对自己文化的毁灭,对祖宗的不敬,这是不孝的子孙。
所以老子也讲:「人法地」,人要效法地,我们效法地干什么?地有什么值得学的?为什么要效法地,要跟地学呢?昨天晚上还跟一位同学谈到,你看大地生长万物,生生不已,最后你死亡了也归到大地上去。它毒药也生,好的坏的都生,大地生青菜萝卜,都是它生养给我们吃,我们还给它的是什么?大小便。它也绝不生气,这样大的厚德,这样大的精神,包容一切,所以人要效法地。
老子说地还不算伟大,地要效法天,那个天永远勤劳不息地在转,你看太阳啊,月亮啊,地球啊,风云雷雨啊,一天到晚都在转在变,而且永远不停息的。那么这个天啊,谁在推动银河系统转呢?有一个东西,西方人叫做上帝,叫做主,东方叫它菩萨,或者叫它玉皇大帝,叫它盘古老王,名词多得很,反正有个东西,这个东西叫做道,「天法道」。那么道要跟谁学呢?「道法自然」,不必跟人家学,道自己是本然的,所以叫自然,也就是道法自然。现在「自然」变成一个名词了,老子那个时候没有「自然」这个专门名词,那个时候的古文,自者自己也,然者本然也,所以叫做自然,自己本身就是道法自然。
那么道法自然是什么呢?至诚不息,真正的至诚是一念专精,没有休息。所以有些人学佛打坐做工夫,乃至于念佛,不管你信哪一个宗教,要一念万年,万年一念,那是至诚不息,叫做定。你做不做得到?「是故诚者,天之道」,要做到你就懂了。所以一切始终在恒动之中,永远的恒动,所以至诚是天之道,天之道是至诚不息。
「思诚者,人之道也」,我们现在是人,人想要回转到天道是要修养才行,所以先要做到「思诚」。孟子这一句话、这个立场,一切宗教家的祷告,乃至佛家的念佛,普通人的打坐,密宗的修观想,都是属于「思诚」,也就是思想集中统一,达到一个专一的境界。达到这个境界是人道的基本修养,也就是一般人所讲修定,不散乱不昏沉所达到的境界。所以普通学佛的说这个人会打坐,一定定好多天,其实那算什么?那只是人道而已。佛法也那么讲,修四加行得了定,叫做世第一法,是人世间最高的境界而已。至于超越人世间的境界,那要另外修过,那是天之道。虽然这样讲,但是你们不要妄自聪明,认为只要达到专一就不需要修定了,那样你们更糟糕了。所以做到了思诚还只是世第一法。
《孟子》下面再告诉我们,「至诚而不动者,未之有也;不诚,未有能动者也」。刚才我说过中国文化不是讲静态的,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化静态是死态;中国文化是活态的,绝对不是静态。同样道理,物理世界的静就在动之中。《易经系传》上有两句话,「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」,所以真的至诚到了,感而遂通,就是「神而通之」,也就是智慧。本体本来是寂然不动的,这个不动不是死的不动,而是寂然不动,一感就通。
有人说信上帝那么久了,拜佛也拜了那么久,怎么求怎么不通,那是什么道理啊?你把《孟子》多读几遍就知道了,因为「反身不诚」,你不诚乎心,没有从「思诚」入手,当然不会有感应。所以孟子说,真做到至诚也等于所谓定,至诚而不动者不可能,一定感通,所以「至诚之道可以前知」。
什么叫做诚?空灵也叫做诚,一念空灵到极点那也是至诚,那是真至诚。至诚之道自然就万事可以前知。所以你说中国儒家有没有神通?有神通啊,孔子神通的秘诀就是寂然不动,你做到了寂然不动就感而遂通,这是孔子传你神通的秘诀。孔子的孙子子思也讲了神通的秘诀,「至诚之道可以前知」。孟子也传了神通,「至诚而不动者,未之有也」,有至诚一定动,感而遂通。相反的,他说如果不诚而想能有感通,那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这一段对于诚的研究,我说加在《孟子》这个地方是很严重的问题。在《离娄篇》的上篇,一直是讲帝王学,政治哲学,政治道德最高的一个形态,一个目标。换句话说,也就是告诉后世人如何才是王道施政最高的修养境界。孟子一直认为,战国当时这些君王、诸侯们太糟糕了,而孟子的存心是拯救民族的文化。前面所讲都是具体的辩论,中间为什么又加了这一段,专门说理论性的至诚呢?他认为一个领导人的修养必须要从内在自动自发,做到至诚的修养才行。不过,这个至诚有层次,有真实的工夫,不只是理念上的思想。
这个道理就要配合曾子的《大学》了,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」;《大学》里还有一句话,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」。所以我强调说,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教育是有一个目标的,这个目标不是为了考试,也不是为了留学,而是为了完成人格,如何成为一个大人;够不上的都是小人,小人就是没有长大的孩子。如何够得上是一个长大的大人呢?《大学》提出来,《中庸》提出来,《孟子》这一段也提出来,不管是什么人都以修身为本,这是基本的修养。人的基础没有打好,连做一个普通人都没有资格,何况做一个非凡的人而且要领导一般普通的人呢?孟子的重点、重心在这一段话,重点在这个地方插进来,大家要特别搞清楚上下文。
《孟子与离娄》二老归服仁政
孟子曰:「伯夷辟纣,居北海之滨,闻文王作,兴曰:‘盍归乎来!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太公辟纣,居东海之滨,闻文王作,兴曰:‘盍归乎来!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二老者,天下之大老也,而归之,是天下之父归之也。天下之父归之,其子焉往?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,七年之内,必为政于天下矣。」
孟子前面插了一段最高的政治道德修养,也就是人生基本的修养。接着再说历史的经验,历史的证明。他说商周之间因纣王无道,那个时候「伯夷辟纣」。伯夷虽说是商朝的亲王,但他看不惯纣王这个皇帝,只好避开。中国上古的宗法社会,因为祖宗的传统,在自己家族之间不能反叛,只好自己隐去,「居北海之滨」,这个北海是哪里搞不清楚,不过晓得他避开了。换句话说,他跑到北方落伍的地区去隐居了。后来听到文王行仁政,「兴曰」,很高兴地说,「盍归乎来」,我也想到他那边去了。文王是反对纣王的哦,他是为了原则而放弃了亲属的一切关系,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而有所作为,因为文王是走传统文化精神路线的。
「吾闻西伯」,「西伯」是文王当时的官位,「善养老者」,这个注意啊,读古书这个观念要搞清楚,不是看到养老就想到养老院。古人所讲的养老,就是当时的君王非常注重国家人民的福利,非常爱民。我们现在所常引用的《大同篇》中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的所有观念,都包括在养老这个名词里,这一点特别特别注意。「善养老者」是注重整个社会民生的问题,所以他认为文王是在行仁政,真正爱国爱民的,因同意他而来,并不是来投降。孟子先说明了这一条,这是一件历史的事。
「太公辟纣,居东海之滨」,姜太公就是吕尚,姜是他封地的名称。姜太公七十多岁才碰到文王,文王比他年纪大,周武王起来革命的时候也有八十多岁。古人是越老越是宝,现在越老越是草,时代不同了。至于姜太公居东海之滨这件事,也没有办法确定地点。由历史记载证明,姜太公原来在东海之滨,山东这一边,后来听到文王起来,就向西部走,到渭水之滨钓鱼去了。
「闻文王作,兴曰:盍归乎来!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」,重复的文字写两段,是孟子的啰唆,如果我做国文老师啊,就把它扛掉,把伯夷跟姜太公并在一起,加几句话就解决了。孟子写得太啰唆了,但是古文是为了读诵,能朗朗上口,唱歌一样念,多一番念,多一番味道,所以他写了两段。再说呢,写两段要提起你注意,加上历史的经验,加重那个语气,光写一段容易马虎过去。
他的结论,「二老者」,中国文化这个老不一定是年纪大,假使退回去一百年,年纪轻的大臣对有功于天下的大官称某老,那是表示恭敬。现代的人叫你老啊,那表示应该报销了,就是完了的代号。古人称你老是绝对恭敬的称呼。在古代那个时候人都很长寿,现在西方的文化医药进步了,活到七八十不算什么。你查周朝的历史,姜太公八九十岁才成功,周文王都活到近一百岁啊,尧啊、舜啊都差不多啊。那个时候又没有盘尼西林,又没有什么消炎的药,那又怎么讲法呢?所以历史很难讲,哪个叫进步?哪个叫退步?我是搞不清楚的。
孟子说「二老者,天下之大老也,而归之」,结果都来拥护周文王,「是天下之父归之也」。什么叫父啊?凡是思想可以领导天下,道德可以领导天下,风气足以影响到天下的,叫做天下之父,也就是老前辈的意思。你们青年同学们注意哦,常常看到古书上的序文,写的是「某某某甫序于唐贞观三年」。序就是序,为什么来个甫序?甫者父也,父者甫也,父又代表男人,甫序就是男子大丈夫的序。这种文字蛮别扭的吧?可是古人就喜欢这样。譬如有一个人写「王大德父书」,年轻人一定以为这一篇文章是王大德的爸爸写的。错了!这是王大德本人写的,他自称父,意思是大丈夫男子汉写的。这是古人的啰唆,旧的观念,站在那个时代是必然的道理。等于现在小姐们出来穿高跟鞋,也是必然的道理。现在看起来古书序文好啰唆,有时候很想把甫字拿掉,印书也可以少一个字啊,节省一点。古人对这个很看重,所以父字的道理就是这样。
「天下之父归之,其子焉往」,大老们都前来拥护文王,下面的子民——就是老百姓,对老百姓有仁慈的爱才称子民,这是中国文化爱人的精神。天下的大老们都归向文王了,他们的子民去哪里啊?当然都一同归向文王了。
因此孟子的结论说,现在的诸侯,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「行文王之政」,效法文王,天下就有救了;当然不能完全跟文王学,完全跟文王学,学得像王安石一样,那就糟糕了,就是食古而不化。所以效法文王是效法那个精神。在孟子当时的估计,「七年之内,必为政于天下矣」,注意这个话,不是讲呆板的七年或五年,那是孟子当时的估计。以现在的观念来说,就是必定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效果。